宋高宗趙構半年三到鎮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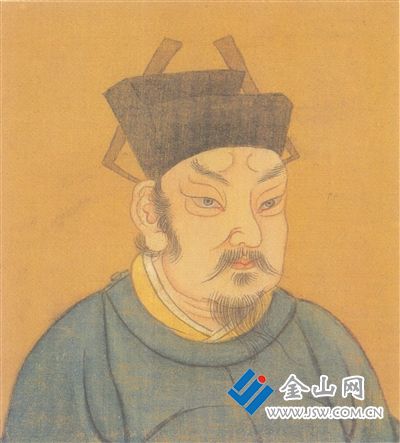
宋高宗趙構像(清人繪)

高宗依托鎮江建都臨安
□ 沈伯素
趙構出生和生活于國家危難之季,靖康二年(1127),北宋滅亡,二帝被俘,在金人不斷南侵的危急情況下,他作為徽宗第九子,登基稱帝,改元建炎,是為南宋高宗。但是,沒有都城,沒有宮殿,在金人的脅迫和追逐之下,他專事奔逃,這便發生了他半年內三到鎮江的故事。
一到鎮江
建炎三年(1129)已經登基第三年的趙構,二月初二,聽說金人陷天長軍,正奔襲揚州。在揚州躲了一年多的他,眼看蹲不下去,慌忙披甲上馬,身邊只有都統制王淵等五六人。因慌張急躁,一位衛士說了他不中聽的話,他竟拔劍將衛士砍死。他到達江邊,對一小船許以重賞,上船渡到對岸的西津渡。他單人匹馬渡江登岸時,身邊竟無一人跟隨。上岸后,獨自走進岸邊的水帝廟里暫歇,就地在靴子上蹭干了劍上的血。鎮江府守臣錢伯言驚悉皇帝到了西津渡,連忙派府兵把他迎到府治,他這才稍有安定。
那時是二月初,天氣乍暖還寒,驚恐加上冷凍,使他顯得十分狼狽。當晚宿于府治時,因跟在后面渡江的隨行均未帶寢具,他“以一貂皮自隨,臥覆各半”。睡前還環顧四周,問附近有無“近上宗室”者。其時,一位名叫“士粲”的曹官說自己就是,皇帝感到了一點溫暖,當即“召士粲同寢”,并解“所御綿背心賜之”。大概因為他心里記得,鎮江是他老爹徽宗的“潛邸”。次日,文武官員陸續來到他的臨時避難所,驚魂未定的皇帝問曰:“姑留此,或徑趨浙中耶?”就留在鎮江還是南去浙江的問題發問。這一問,等于發起一場關于建都何處的大討論。吏部尚書呂頤浩說:“愿且留此,為江北聲援。”這一意見得到戶部尚書葉夢得等三位大臣的支持。見多數大臣主張留在鎮江,皇帝說:“既然這樣,我們立即一同去江邊,經畫一下江防大事。”但是不多會,御營都統制王淵入對:“暫駐鎮江止捍得一處,若金人自通州渡,先據姑蘇,將若之?何不如錢塘有重江之阻?”這個意見得到了諸內侍的贊成。皇帝把這一意見告訴大臣們,事情就這樣定了,繼續南逃,目的地是錢塘(即杭州)。
這是趙構第一次來到鎮江。雖然只在鎮江江待了一兩天,但辦了兩件大事,一是討論、確定了下一步的計劃;二是鑒于鎮江對于軍事防守的重要地位,臨走時作了重要安排:他命令大臣呂頤浩為資政殿大學士充江浙制置使;大臣劉光世為行在五軍制置使,屯鎮江府,控扼江口。
二到鎮江
趙構第二次來鎮江,是他在杭州待了一個月之后。
因為在揚州時,侍衛官膚敏曾多次對他說:“揚州非駐蹕地,請早幸江寧。”他一直記得膚敏的話,到杭州后又專門召膚敏問及此事,膚敏表示杭州也不宜建都,三次以江寧為請。當年三月初一,因聽說那時金人已經北退,他很快下詔:“當進幸江寧府,經理中原。”
此詔剛發出,杭州突然發生了一件令他驚魂落魄的事:三月初五,扈從統制苗傅、威州刺史劉正彥二人謀反,殺掉了皇帝的親信都統制王淵,逼迫皇帝遜位,要求由他的幼子接位,太后垂簾同聽政。這使他不僅不能趕赴江寧,還不得不移居顯寧寺,退而稱睿圣仁孝皇帝。
趙構讓位的事引起了大臣們普遍不滿,四月初一,也就是他讓位25天以后,太后還政,趙構復位。
復位后,趙構仍念念不忘江寧,不日就從杭州急急起程北上。同時,命韓世忠為江浙制置使,劉光世追討逃跑中的苗傅和劉正彥。五月初四,也就是皇帝離杭州四天以后,再次到達鎮江。
此次北上,他經過平江、常州各城都未曾逗留,但到達鎮江,卻不急于離開,他清楚:鎮江“內控江、湖,北拒淮、泗,山川形勝,自昔用武處”。雖被金兵追得喪魂落魄,關于鎮江的江防要事,不能不加顧及。在鎮江時,難免親自去檢查一番。再有,他還費神于一樁冤假錯案。
建炎元年(1127)八月,一代學生運動領袖、愛國者、民族英雄鎮江人陳東(具體籍貫為丹陽珥陵)因力主抗金,反對投降、退讓,得罪了奸臣黃潛善等,經趙構同意,被殺害于集市。此次皇帝來到陳東的家鄉,隨行的翰林學士滕康請去祭掃陳東墓。他立即同意,并命御筆張愨致祭;還告諭當地執政,說明陳東是忠諫而死,“厚恤其家焉”。事情說明,時隔兩年,趙構對于當時決定殺掉陳東是后悔了。為了平反,他還追贈陳東為朝奉郎、秘閣修撰,賜錢五百緡、祭墓田四十頃。
三到鎮江
趙構于五月初八到達江寧府,將府名改為建康。兩個多月后,苗傅、劉正彥伏誅了;杭州也升為臨安府了;本該繼續待下去,在建康正式建都。但是,金人又興兵大肆南侵。
鑒于“敵人迫逐,未有寧息之期”,皇帝一時又沒了主張,于閏八月初一出詔,就“移蹕之地”,要大臣討論上哪去為好?武官張俊和辛企宗,都勸皇帝去長沙,韓世忠卻不同意,說:“國家已失河北、山東,若又棄江、淮,更有何地!”宰相呂頤浩發愿:“臣頤浩留常、潤死守。”皇帝最后決定還是去臨安。離開江寧后,建炎三年閏八月初八那天,是他在半年內第三次到達鎮江。
這次蒞鎮,安排江防要事是他的重點考慮。為此,他絞盡腦汁,做了兩件事:一是因獲悉金人在梁山泊造舟,恐其由海道來襲。為加強江防,親自在登云門外檢閱了水軍。二是移浙西安撫司于鎮江府,著劉光世屯兵鎮江,且安排韓世忠充兩浙、江、淮守御使,并交代要兼顧圌山的防守。兩事以后,他又想起那件冤案,再次賜陳東家金。這次,他在鎮江住了四天。
皇帝趙構在歷史上頗受爭議,但他雖然軟弱畏敵,卻絕非癡呆。一般高官來鎮江,主要是為游覽或視察,他則是逃跑路過性質。但他如同軍事家、史學家一般,對鎮江的軍事地位有著清醒的認識。他深知“京口控扼大江,是為浙西門戶”。于任何地方建都,鎮江都是重要依托。他三到鎮江的種種表現,起碼說明了以下兩點:一是在建都問題上,他初到鎮江時,曾問大臣“姑留此,或徑趨浙中耶?”這至少對鎮江是否可作選項曾有過一閃念。二是他反復部署鎮江江防,對后來在臨安建都起到了重要的依托作用。他對鎮江防守的重視和安排,受到史家的注重與肯定,《讀史方輿紀要》稱:“宋南渡以后,常駐重軍于此(指鎮江),以控江口。”這對于南宋百多年的防守和安全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責任編輯:阿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