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文物古跡里還原鎮江的歷史
——訪《鎮江通史》主編李恒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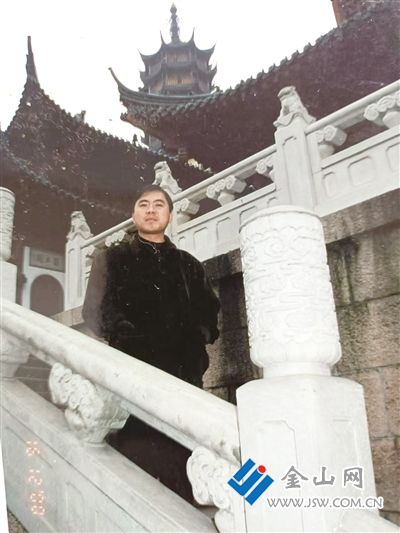

花 蕾
李恒全:南京師范大學社會發展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長期從事先秦秦漢史研究,對先秦秦漢時期的土地制度、賦役制度、商品經濟、生產力狀況、繼承制度等問題有較為深入的研究,先后發表學術論文四十余篇,出版專著與合著多部,主持完成國家、省部級科研項目多項。中國秦漢史學會理事、江蘇省六朝史研究會理事、南京歷史學會副會長。
一早就鐘愛歷史
李恒全1968年出生于江蘇睢寧。睢寧是出了名的貧困縣,所以李恒全的求學之路就走得格外辛苦。他小學和初中就讀的是村里的戴帽子中小學。村辦學校教學質量差,一年也考不出幾個學生。李恒全有個表哥,成績非常好,考上了大學,這位表哥對他影響很大。和其他瞄準可以轉戶口分配工作的中專的農村同學不同,李恒全一早就制定了讀高中考大學的目標,老師講得不清楚,他就自己努力自學。中考他以遠超中師的分數,成為當時全縣唯一一個從村辦學校考進睢寧中學的學生。
進了高中,沒怎么好好學習過英語的他英語有點跟不上。跟不上也不怕,為求學吃過苦頭的他努力了幾個月,也就適應了。據考證,睢寧就是古代的下邳,下邳在春秋戰國時已建城,到三國時達到巔峰,有“一部三國史,半部下邳城”“兩漢看三國,三國看下邳”之說。故鄉的歷史文化底蘊潛移默化地影響了李恒全的喜好,所有的科目中他最喜歡歷史,所以分科時他毫不猶豫地選擇了文科。高中他遇到了一位特別喜歡的歷史老師,老師課講得好,藏書也多,作為歷史課代表的李恒全也很得老師偏愛,在老師那借閱了大量歷史類書籍。1987年,李恒全以高考文科成績全班第一、全縣第二的成績考上了蘇州大學歷史系。大學時其實李恒全還沒明確自己研究的具體方向,他把所有的課余時間花在了閱讀上,沒事就泡在圖書館,歷史學理論、文學名著、哲學、法律……來者不拒,一口氣讀了大量藏書。回看來時路,李恒全覺得大學的這段瘋狂閱讀的經歷,對自己形成思維方式,獨立思考、拓寬眼界有很大的幫助。一心沉浸讀書中,臨到畢業,看到有同學考上研究生,他才發現,讀書過程中有不少問題自己想不透,原來自己也想讀研的,但是在校報考已經來不及了。
大學畢業,李恒全回到睢寧,在下面城鎮的凌城中學當了一名歷史老師,一邊工作,一邊準備考研。當年學校有規定,必須工作滿五年以上才能報考研究生,而且每個學校還有名額限制,一年只允許一人報考。當年城鎮中學老師的生活比較單調,很多同事下了班會聚在一起打打牌,一直閉門讀書備考的李恒全一時竟成了另類,同事們有時會調侃他一下。1997年,李恒全考上了江西師范大學專門史專業。
瞄準秦漢歷史
讀研時,李恒全發現本科時的閱讀積累對自己搞研究幫助很多,很多問題當年就有接觸,有思考,所以讀碩階段他很快找到了自己的研究方向:秦漢史。2000年碩士研究生畢業,他分配到江蘇省社會科學院工作。2004年他考進南京師范大學專業史專業,繼續攻讀博士學位。
找準研究方向,李恒全陸續發表了多篇論文:《也談西漢田稅的征收方式問題》《漢代田稅百畝征收說確難成立》《試述漢代官營手工業中的商品生產》《試述漢代私營手工業的商品生產》《鐵農具和牛耕導致春秋戰國土地制度變革說質疑》《對戰國田稅征收方式的一種新解讀》《漢代商品生產的結構及其特點》《漢初限田制與田稅征收方式——對張家山漢簡再研究》《秦漢芻稾稅征收方式再探》《漢代限田制說》《秦漢商品經濟研究的新成果》《從張家山漢簡看西漢以畝計征的田稅征收方式》《漢文帝未曾連續十余年不收田租再論》《從出土簡牘看秦漢時期的戶稅征收》《從天長紀莊木牘看漢代的徭役制度》《從出土簡牘看秦漢家庭繼承制度》《從張家山漢簡看漢初家產等級繼承制》《井田制變革前農業耕作技術的緩慢發展》《秦漢新出簡牘中的“輿田”和“稅田”》《從新出簡牘看秦田租的征收方式》《從新出簡牘看秦的土地私有制》《從出土簡牘看先秦秦漢時期的畝制》《“賜民爵”“賜牛酒”與漢代普惠性社會福利研究》《論秦漢田稅征收方式及其變化過程》等論文數十篇。其中《鐵農具和牛耕導致春秋戰國土地制度變革說質疑》因對傳統學術觀點提出了挑戰,在國內文史界影響較大,《金陵晚報》曾派記者采訪,推出版面介紹。出版專著《戰國秦漢經濟問題考論》,參與《六朝文化概論》《南京歷代風華》《江蘇通史》等著作的編纂工作。主持完成《出土簡牘與戰國秦漢土地制度研究》《簡牘與戰國土地制度研究》《秦漢三國簡牘中的賦役制度研究》等國家、省部級科研項目。專著《戰國秦漢經濟問題考論》獲得江蘇省高校哲學社會科學第九屆優秀成果獎。
2000年7月李恒全從江西師范大學專門史專業碩士研究生畢業,到了江蘇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從事研究工作。由于距離鎮江較近,經常在假期和周末來鎮江游覽,可以說常來常往。
2008年5月李恒全調到南京師范大學社會發展學院歷史系工作后,多次帶領學生來鎮江游玩,并多次陪同外地來寧的專家學者到鎮江參觀,鎮江的金山、焦山、北固山、茅山、西津渡、宗澤墓、劉賈墓、丹陽南朝石刻等古跡,以及鎮江的鍋蓋面、肴肉等美食都給他留下了深刻的影響。印象最深的一次是帶著同行探訪漢荊王劉賈墓,打聽了很多人才找到地方。“萬萬沒想到去劉賈墓要從那么窄的一條小巷子進去,最后豁然開朗。”
關于《鎮江通史》先秦秦漢卷
參與過《江蘇通史》的編纂,李恒全是六朝卷的編輯,閱讀了大量關于鎮江的歷史文獻,對鎮江的文物古跡,歷史遺存非常熟悉。“鎮江文史資源豐富,有著豐富的文化底蘊。” 李恒全說,西周時期,周人南渡帶來了中原先進的文化。當時,吳國的中心地帶位于鎮江丹徒、丹陽域內,鎮江丹徒龍泉鄉煙墩山出土宜侯夨簋,宜侯夨簋是中原文化擴展到江南地區的物證。受到中原文化的強烈影響,大量青銅禮器特別是具有地方特色的青銅器的發現,標志著本地青銅冶鑄業的快速發展。鎮江是季扎的出生地。季札是春秋時期吳國著名的政治家、外交家和音樂家,季札品德高尚,三度讓國,并富于才學、修養,其美學觀點對儒家美學思想有重要影響,他廣交當世賢士,對提高華夏文化作出了重要貢獻。鎮江是秦始皇巡游的重點區域,秦始皇在東巡時經過鎮江到會稽。公元前196年荊王劉賈在平定淮南王黥布的作戰中遇害,死后葬于鎮江。西漢前期,吳王劉濞聯合楚,趙等六國發動“七國之亂”,后劉濞敗亡丹徒,為東越軍所殺。鎮江也是三國孫氏政權發跡之地。
2019年,《鎮江通史》編纂工作啟動,常務副總主編姜小青牽頭讓李恒全負責先秦秦漢部分的編纂工作。“這段時期的鎮江歷史編纂特別難。因為當時的經濟文化中心主要還在黃河流域。關于這個時期鎮江歷史的文獻寥寥無幾,要將和鎮江有關系的各方面的情況囊括其中,難度很大。”
李恒全的處理辦法是盡量利用出土文獻和考古資源。將歷史傳說進行考證,也利用起來。有一份材料,說一分話,為此,他還把南京博物館的一位朋友拖進來一起研究。
鎮江的一些考古遺址給李恒全的編纂提供了很多支持:比如位于經開區丁崗鎮的孫家村遺址是西周早中期至春秋晚期吳國重要鑄銅遺址,為周代冶金考古研究提供了新的資料,對吳文化歷史研究有重要意義。比如斷山墩遺址,是西周時期吳國土著人居住的村遺址,是蘇南最大且較為完整的古代先民土著村落遺址,發掘出土繩紋、編織紋、梯格形印紋、云雷紋、回紋等60多種紋飾的夾砂紅陶和灰陶及少數原始青瓷;遺址中發現了夯土臺基和柱礎,臺基底部、房屋柱礎之間埋有人骨架,房中有灶以及大量燒土和制坯用的陶板子、不合格的廢棄陶器,是鎮江地區吳文化重要遺存。還有煙墩山西周古墓遺址更不用說了,發掘出宜侯夨簋,簋內有銘文120余字,記載了宜侯夨受封的情況,是研究西周分封制,以及周王室與長江下游地區關系的重要資料。此外還有鐵甕城遺址,保存遺跡完整,文化內涵豐富,作為地方政治中心的治所,歷經晉、唐直至明、清,已有1700多年的歷史。鐵甕城遺址的發掘,為研究三國時期的歷史文化提供了重要的實物資料……這些文物古跡遺址為李恒全的編纂工作提供了非常大的幫助,據李恒全介紹,目前,《鎮江通史》的先秦秦漢部分已經完成30多萬字,可以說初步完成了任務。
責任編輯:阿君

